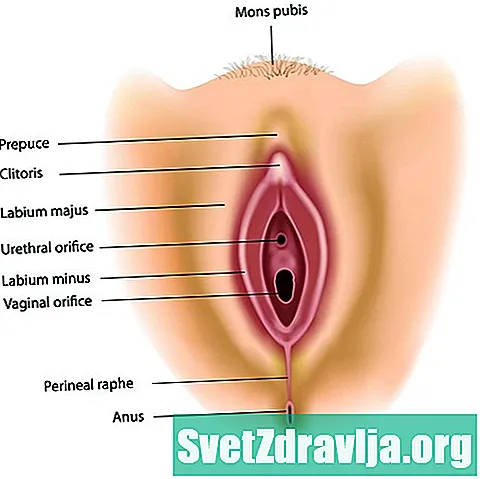产后PTSD是真实的。我应该知道-我住了

内容
- 不久以前,我就出生了那一天,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,最艰难的时期。
- 那年11月的一天,一家备用瑜伽馆改建成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,在那里我度过了女儿一生的头24小时,双手伸直并束缚。
- 我的女儿原定于7月一个非常正常的早晨通过剖腹产分娩。
- 在手术室里,我屏住呼吸,深呼吸。我知道这项技术可以避免恐慌。
- 当我退缩时,我的孩子出现并大声喊叫。当我们的身体被撕裂时,我们的意识状态发生了逆转。
- 我把自己举到地上,在剪贴板上写道:“我的宝贝?”我在窒息管周围咕unt一声,用力刺破了纸张。
- 最糟糕的事情是永远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。没有人会估计– {textend} 2天还是2个月?
- 几个月后,我的精神科医生向我祝贺我对重症监护病房婴儿的处理情况。我已经很好地消除了世界末日的恐惧,以至于这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也看不到我。
- 我渴望瑜伽-{textend},我每周几个小时都没有去看医生,父母有罪恶感,也一直害怕我的孩子不舒服,这让我感到不安。
- 上完课后,我们都呆在后面,把自己布置在房间的四周。计划了一个特殊的仪式,以纪念一个季节的结束和开始。
像瑜伽姿势这样简单的事情就足以让我回想起。

“闭上你的眼睛。放松脚趾,双腿,背部,腹部。放松肩膀,手臂,手和手指。深吸一口气,在嘴唇上露出微笑。这是你的Savasana。”
我在背上,双腿张开,膝盖弯曲,手臂在我的身边,手掌向上。香气弥漫的香气弥漫着辛辣,多尘的气味。这种气味与潮湿的叶子和橡子相匹配,修补了工作室门外的车道。
但是,一个简单的触发条件就足以窃取我的时间:“我感觉自己正在生孩子,”另一位学生说。
不久以前,我就出生了那一天,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,最艰难的时期。
第二年,我回到瑜伽,这是身体和精神康复的众多步骤之一。但是,“分娩”一词以及秋天那天下午我在瑜伽垫上的脆弱位置,共同引发了强烈的反跳和恐慌发作。
突然,我不在昏暗的瑜伽工作室中,在竹地板上的蓝色瑜伽垫上,披着午后的影子。我当时正在医院的手术台上,被束缚着瘫痪了一半,听着刚出生的女儿的哭声,然后陷入了麻醉的黑夜。
似乎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问:“她还好吗?”但我害怕听到答案。
在长时间的黑夜之间,我移到意识表面片刻,升起足以看到光。我的眼睛睁开,耳朵听了几句话,但我没有醒来。
我不会真正地醒来几个月,因为沮丧,焦虑,重症监护病房之夜和新生儿的疯狂迷雾中开车。
那年11月的一天,一家备用瑜伽馆改建成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,在那里我度过了女儿一生的头24小时,双手伸直并束缚。
“永恒的嗡嗡”在瑜伽室里演奏,每一次深沉的mo吟都会使我的下巴更加紧。我的嘴紧紧against住,喘着粗气。
一小群瑜伽学生在萨瓦萨纳(Savasana)休息,但我躺在地狱般的战争监狱中。我的喉咙cho住了,想起了呼吸管以及我恳求我整个身体说话的方式,只是被窒息和克制。
我的手臂和拳头绷紧了幻影的纽带。我出汗并努力保持呼吸,直到最后的“恶心”让我自由了,然后我才离开工作室。
那天晚上,我的嘴里感觉参差不齐。我检查了浴室镜子。
“天哪,我咬了牙。”
我与现在如此疏远,直到几个小时后才注意到:那天下午我躺在萨瓦萨纳(Savasana)时,我咬紧牙关,以至于磨碎了一颗臼齿。
我的女儿原定于7月一个非常正常的早晨通过剖腹产分娩。
我和朋友发短信,和丈夫拍照,并咨询麻醉师。
当我们浏览同意书时,我注视着这种出生叙事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。在什么情况下我可能需要插管并全身麻醉?
不,我的丈夫和我会在一起在寒冷的手术室里,我们对凌乱的碎片的看法被宽大的蓝色床单遮盖了。经过一阵怪异的,麻木的拉扯我的腹部之后,一个痉挛的新生儿将被放在我的脸旁以作初吻。
这是我计划的。但是,哦,它确实如此横向。
在手术室里,我屏住呼吸,深呼吸。我知道这项技术可以避免恐慌。
产科医生在我的肚子上做了第一道浅切,然后停了下来。他冲破了蓝床单的墙,向我和我丈夫讲话。他说话高效而镇定,所有杂物都疏散了整个房间。
“我可以看到胎盘已经通过子宫生长了。当我们切开将婴儿带出去时,我希望会有很多出血。我们可能必须做子宫切除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等待几分钟才能将血液带到手术室。”
他指示:“在我们将您放下并完成手术之前,我要请您丈夫离开。” “任何问题?”
这么多的问题。
“没有?好。”
我停止深呼吸。当我的眼睛从一个天花板广场飞到另一个天花板广场时,我因恐惧而cho之以鼻,无法看清我所集中的恐惧。单独。占据。人质。
当我退缩时,我的孩子出现并大声喊叫。当我们的身体被撕裂时,我们的意识状态发生了逆转。
当我沉入黑色子宫中时,她把我换成碎片。没有人告诉我她是否还好。
数小时后,我在感觉像是战区的麻醉后护理部门醒来。想象一下1983年贝鲁特的新闻镜头-{textend}大屠杀,尖叫,警笛声。手术后醒来时,我发誓我以为自己在残骸中。
午后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投射出我周围的一切。我的手被绑在床上,被插了管,接下来的24小时与噩梦没有区别。
不露面的护士在我上方徘徊,在床外。当我飘浮进出意识时,它们渐入渐出。
我把自己举到地上,在剪贴板上写道:“我的宝贝?”我在窒息管周围咕unt一声,用力刺破了纸张。
剪影说:“我需要你放松。” “我们会找到您的孩子的。”
我浸在表面下。我努力保持清醒,交流,保留信息。
失血,输血,子宫切除术,托儿所,婴儿...
大约凌晨2点-{textend},在她离开我半天后-{textend}我与女儿面对面。一位新生儿护士使她整个医院都对我充满了活力。我的双手仍然束缚,我只能用鼻子抚摸她的脸,然后再次把她带走。
第二天早上,我仍然被囚禁在PACU,而电梯和走廊都在,婴儿没有得到足够的氧气。她变成了蓝色,被转移到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。
当我独自一人去产科病房时,她留在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箱子里。至少每天两次,我的丈夫会拜访婴儿,拜访我,再次拜访她,并向我报告他们认为对她有问题的每件事。
最糟糕的事情是永远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。没有人会估计– {textend} 2天还是2个月?
我逃到楼下坐在她的箱子旁边,然后回到我的房间,在那里我遭受了三天的惊恐发作。我回家时她还在NICU。
回到自己床上的第一夜,我无法呼吸。我确定自己会意外地用止痛药和镇静剂杀死自己。
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第二天,我看着婴儿在吃饭时不溺水而挣扎。当我在一家炸鸡连锁店的直通车道发生故障时,我们离医院只有一个街区。
这位直通车司机低声说道:“ my,,want,要吃鸡吗?”
这太荒谬了,无法处理。
几个月后,我的精神科医生向我祝贺我对重症监护病房婴儿的处理情况。我已经很好地消除了世界末日的恐惧,以至于这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也看不到我。
那个秋天,我的祖母去世了,没有情绪激动。我们的猫在圣诞节死了,我向丈夫致以机械慰问。
一年多以来,我的情绪只有在被触发时才可见-{textend},包括去医院看电视,看医院时看电视,看电影的先后顺序,俯卧在瑜伽馆里。
当我看到重症监护病房的图像时,我的存储库中出现了裂缝。我跌入裂缝,回到了婴儿刚出生的头两个星期。
当我看到医疗用具时,我自己回到了医院。回到伊丽莎白与婴儿伊丽莎白。
我可以闻到金属工具的叮当响。我能感觉到防护服和新生儿毯子的僵硬织物。金属婴儿推车周围的一切无处不在。空气磨损了。我能听到监视器发出的蜂鸣声,泵的机械声,微小生物的绝望声。
我渴望瑜伽-{textend},我每周几个小时都没有去看医生,父母有罪恶感,也一直害怕我的孩子不舒服,这让我感到不安。
即使我无法呼吸,即使我丈夫不得不劝我不要每次都跳过瑜伽,我也承诺每周做一次瑜伽。我和老师谈论了我正在经历的事情,分享我的脆弱性具有天主教认罪的救赎品质。
一年多以后,我坐在同一个录音室,经历了最强烈的PTSD闪回。我提醒自己要定期松开牙齿。我特别注意保持脆弱的姿势,着重于自己所在的位置,环境的物理细节:地板,周围的男人和女人,老师的声音。
尽管如此,我还是把房间从昏暗的工作室变成了昏暗的医院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努力释放肌肉的紧张感,并从外部束缚中辨别出这种紧张感。
上完课后,我们都呆在后面,把自己布置在房间的四周。计划了一个特殊的仪式,以纪念一个季节的结束和开始。
我们坐了20分钟,重复了“欧姆” 108次。
我深吸了口气...
喔喔喔喔喔喔喔喔
再一次,我的呼吸急促了……
喔喔喔喔喔喔喔喔
我感觉到冷空气的节奏在流入,被我的腹部转变成温暖而深沉的低沉,我的声音与其他20个人无法区分。
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如此深吸一口气。我正在康复。
安娜·李·贝耶(Anna Lee Beyer)撰写有关心理健康,养育子女的书籍,并为《赫芬顿邮报》,《连身衣》,《生活黑客》,《魅力》等书籍。在Facebook和Twitter上拜访她。